保利證券固收研究 (原文《關于維好將死的傳言》2024年6月19日發布于《國際業務》)
維好是個什麽樣的存在,外債圈內的都心知肚明。他的核心使命,就是在基本上保有類似擔保的增信效力的同時,避免跨境擔保登記的麻煩。
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修訂資本項目外匯業務指引的通知》(匯〔2024〕12號,下稱“《指引》”)于2024年5月6日起實施。第3.5.4.1(7)條規定:“具有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實質構成擔保的維好協議須參照內保外貸管理,境內擔保人承擔法律性質甄別及登記責任。”
在目前的司法實踐和市場認知中,維好的增信效力尚可商榷。但如果維好像跨境擔保一樣也需要在外管辦理登記,則維好的設計目的將消失。維好,這個我國外匯監管現實催生的獨特存在,是否即將走到他生命的盡頭?

我們認爲,近年來的境內外司法案例已表明,維好和擔保之間存在明確的、實質性的區別。按照《指引》的要求進行“法律性質甄別”幷不困難。同時,催生維好的動機不僅持續存在,甚至更加凸顯。在目前維好增信的效力已經相當明確的情况下,在特定場景中使用維好結構依然是外債發行人明智的選擇。
一、維好和擔保之間的實質性區別
在中資境外債幷不悠久的發展歷史中,維好結構不能算是新生事物。2011年6月30日,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爲Zijin Europe International Mining Co Ltd. 的4.8億美元債券提供維好支持,是目前可查的最早案例。同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爲其子公司CNPC Golden Autumn Limited提供維好支持發行了5億人民幣點心債。2012年,金地集團、首創置業、中遠海運、大唐國際、龍源電力、中國信達等高質量發行人隨後跟進。此後,維好結構廣泛應用于境外債券的三大主要板塊:金融機構/央企、地方國企/城投和房地産。國際評級機構授予跨境擔保發行的債券評級通常與擔保人的主體評級一致。而采用維好結構的房地産公司債券評級通常比維好提供人的主體評級低至少一個子級,以反映維好結構信用傳導的不確定性。而城投公司維好債券則通常可以享受與維好提供人主體一致的國際評級。畢竟,城投信用考量的不僅僅是法律實質。更重要的,是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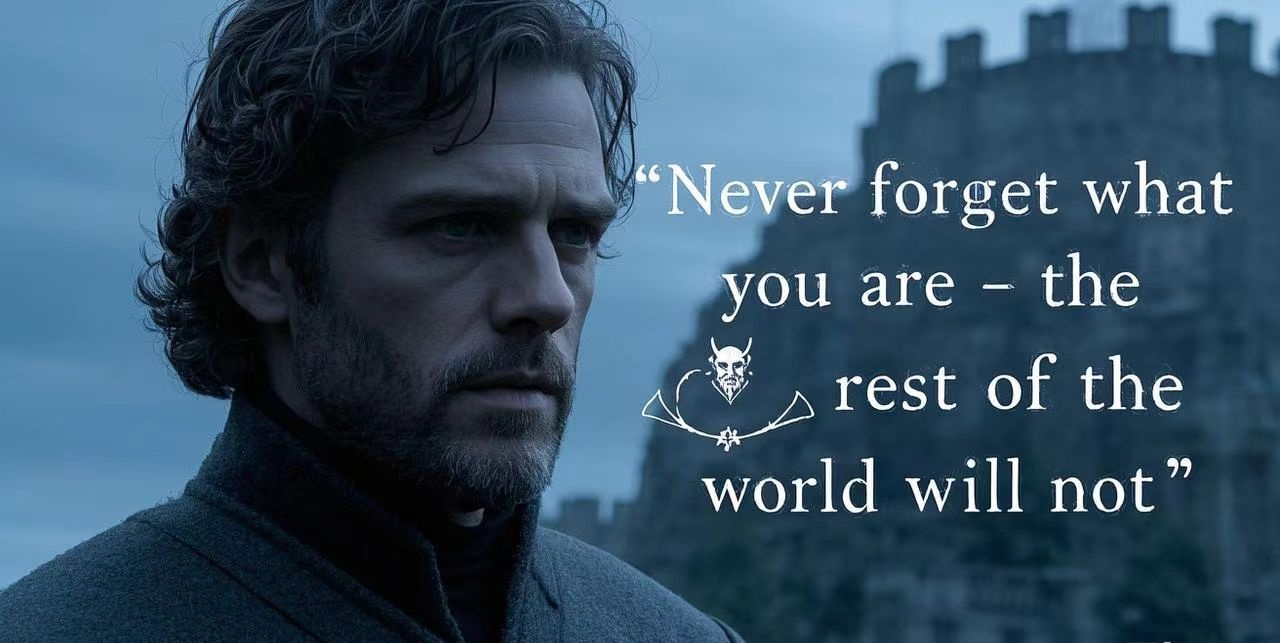
維好協議(Keepwell Agreement)以及配套的股權購買承諾(Equity Interest Purchase Undertaking)通常要求維好提供人維持境外債務人的淨資産爲正值、爲其提供償還債務的流動資金、以及保持其對境外債務人的管控權和所有權等。當履行承諾需要有關部門的批准將資金匯出境外時,維好提供方須盡最大努力尋求批准。十多年來,市場對于維好結構的增信效力的認知主要受到以下標志性案例的影響:
1、國信證券技術性違約
國信證券(海外)于2014年4月發行了12億元離岸人民幣點心債,以國信證券(香港)(“國信香港”)爲擔保人,由內地母公司國信證券提供維好支持。根據維好協議,國信證券(海外)和國信香港必須隨時保證各自至少擁有100萬美元的合幷資産淨值。2016年2月,審計師對國信香港進行的限制性條款測試顯示,公司的合幷資産淨值已經低于100萬美元,幷且持續維持在這個紅綫以下。內地母公司需要對國信香港注資以滿足維好約定的財務條件。母公司早已向中國證監會提交對外注資的申請,但由于當時其正遭受監管調查,該申請遲遲未獲得批准。國信證券點心債技術性違約的消息傳出後,在市場上引起軒然大波。隨後,母公司的注資申請迅速獲批。
國信事件對于擔憂維好結提供人資金出境實操性的投資人來說無疑是一劑强心針。雖然這種倒逼監管的案例是各方博弈妥協的權宜之計,但外債市場此後就有理由相信,境內監管機構在面臨債券違約風險的情况下,不會阻撓維好提供人正常地調撥資金出境以履行維好責任。
2、北大方正債務重整
2019年12月北大方正集團境內債違約,同時觸發了其提供維好增信的美元債券的交叉違約。2020年5月,北大方正集團的債務重整管理人宣布僅對北大方正擔保的境外債券予以債權確認,而對其提供維好增信的5只共17億美元的境外債券不予以債權確認。
這個决定對于維好結構是當頭一棒。無論多麽高妙的設計,如果在債務重整的緊要關頭得不到認可,則一切都是空談。一時間,維好被投資人廣泛質疑,“維好不投”成爲各個投資人風控部門的標準立場。
3、上海華信案
2020年10月,上海金融法院對華信案的判决似乎爲維好扳回一城。2017年10月,上海華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在英屬維京群島設立的關聯實體哲源國際發行了2,991萬歐元債券。時和基金購買了該債券,成爲其登記持有人。華信集團向時和基金出具維好協議,承諾將采取措施使哲源國際維持合幷淨值及足够的流動性。維好協議中明確該承諾幷非擔保,但如果華信集團未能履行義務則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協議還約定其適用英國法律,且爭議由香港法院管轄。
2018年8月,時和基金在香港就華信集團違反維好協議爲由提起訴訟幷取得缺席判决。2019年11月,上海華信進入破産清算程序。2020年1月,香港法院在該案件中承認內地破産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確認了內地破産程序在香港的域外效力。此時,債權人維權的法律路徑有:1)向上海華信破産管理人申報維好債權,如果管理人不確認該債權,再向上海法院提起債權確認之訴。北大方正重組事件後,這個路徑的前景顯得迷霧重重;或2)向上海法院申請執行香港法院的判决,從而迫使破産管理人對認定債權。
債權人明智地選擇了後者,于2020年5月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請認可和執行香港法院的判决。審理中,華信集團抗辯稱:維好協議的本質爲跨境擔保,該擔保行爲未依照內地法規經外管局審批幷登記,執行香港法院的判决將違反內地社會公共利益。法院則認爲,當事人在“維好協議”中所約定的准據法爲英國法律,不能以內地法律關于維好協議性質及效力的判斷作爲認可和執行該香港判决是否違反內地社會公共利益的認定標準,而只應考量認可和執行相關判决的結果是否有悖于本案審理之時的公共利益。該案是內地與香港之間區際司法協助的案件,拒絕認可和執行該判决的“社會公共利益”應作嚴格解釋,通常僅包括認可直接違反內地公共利益之情形。香港法院判决的認可與執行幷不涉及內地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且內地有關外匯管理的規定經歷了不斷變化的過程,華信集團幷未證明執行香港判决如何違反內地公共利益。
華信集團的抗辯直接指向了維好協議的本質:你本來就是個爲繞過外管監管而設置的擦邊球,現在出了事情不是應該後果自負麽,還要法庭給你做主,你好意思麽你?而上海金融法院的判斷足顯睿智:我不去置評那個擦邊球是否妥當, 那個是有關方面的事情,我豈能多嘴。但我這是內地和香港的“區際司法協助”,是大格局你懂不懂?你老賴當初白紙黑字,拿的是真金白銀,也是擦邊球的積極參與方。如今搬出公共利益就想借我的手賴帳,憑啥?你說說,讓你還錢究竟妨礙了哪些“不特定多數人”?你證明不了吧,就知道你證明不了。那我不管了,還錢!
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避開了“維好協議在內地法律下是否有效”這個難題,而是簡單地陳述了一個事實:當事人約定的是英國法和香港管轄權。一旦香港産生了有效判决,沒有特殊的公共利益理由,內地法院就必須執行該判决。
4、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的Harris 法官于2023年5月18日和6月15日分別就諾熙資本訴北大方正案(案件編號:[2023] HKCFI 1350)和花旗集團訴清華紫光案(案件編號:[2023] HKCFI 1572)作出了確認維好協議效力的標志性判决。 法院認爲,如維好提供方證明其盡了最大努力仍無法獲得必要的監管批准以履行其義務,則其維好義務將被免除。在債務重組開始之後,境內維好提供方向境外發行人提供資金的出境申請不再可能獲批,而在進入重組程序之前是有條件獲得監管的審批而履行維好責任的。北大方正案中,部分美元債維好義務的觸發時北大方正已經進入債務重組,法院因而駁回了持有這部分債券的諾熙資本等3家原告的請求。而方正資訊所持債券的相關維好義務在債務重組前已經觸發,法院判定北大方正違反了維好協議,應賠償折算爲人民幣11.54億元的損失。清華紫光則是在維好違約後才進入重組程序,法庭認爲清華紫光在進入重組前沒有盡最大努力履行維好義務,花旗集團作爲信托人代表維好債券持有人獲得勝訴。
諾熙資本等3家北大方正案債券持有者提出上訴幷于2024年5月10日在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獲勝。上訴庭認爲,北大方正可以有不同方式履行維好承諾,幷非所有方式都需要政府審批。法庭列舉了一些不涉及從中國境內往境外跨境匯款亦可履行維好承諾的方式:要求不受中國法有關限制的第三方對北大方正債務人提供財務支持、利用境外資源協助還款、開展境外再融資等。維好協議觸發的時間點是否在維好提供人債務重整程序啓動之前幷不影響維好提供人承擔的維好義務。法院因而宣布北大方正違反了維好協議,須承擔債券持有人本息損失總計約17億美元。
維好協議通常都約定爭議解决的准據法爲英國法,幷約定香港法院具有管轄權。假設北大方正的判例最終不被香港終審法院推翻(尚不知北大方正是否已經提出上訴),則香港司法體系下維好協議的有效性將得到進一步明確和加强。無論維好協議觸發時維好提供人是否已經處于債務重組的狀態,證明其已經盡最大努力滿足維好承諾均不容易,維好提供人很難以此來逃避履行維好責任。據悉,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將就北大方正債務人的香港維好協議判决在境內獲得認可事宜進行開庭審理。華信案例中上海金融法院展示出的對于香港判决的尊重很可能會影響北京法院的斟酌。特別是2024年1月《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生效後,北京法院要在執行層面推翻香港的判决,更需要充分的理由。
二、維好協議幷不實質構成擔保
如果北京法院最終確認北大方正維好債券持有人的債權,則自2020年5月北大方正案而起的對于維好結構的信任危機將告一段落。至少在司法層面,維好債券持有人的權益將得到明確的保障。然而,這是否意味著維好協議符合《指引》第3.5.4.1(7)條“具有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實質構成擔保”的定義?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維好提供人所承擔的法律義務與擔保人有本質上的不同。擔保人直接保障債券本息的按時支付,而維好提供人僅保障債務人具有足够的清償能力。債權人可以直接向擔保人追償,而維好提供人僅對其未履行維好義務而造成的損失做出賠償。因此,維好提供人賠償的責任和金額受限于其違約行爲和債權人的實際損失之間的因果關聯。如果維好提供人履行了維好承諾,哪怕債務人拒絕支付債券本息,維好提供人也沒有責任。或者,維好提供人沒有履行維好承諾,但是債權人自身的行爲也促成了最終的實際損失,則維好提供人僅應承擔部分損失。
另外,維好提供人只要“盡最大努力”去履行違好承諾就可以避免被視作違約。雖然香港上訴法庭已經把“盡最大努力”的門檻抬得很高,但畢竟達到這個門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擔保人則沒有相同的機會逃避責任。
再則,擔保人責任的觸發點是債券違約,而維好責任的觸發點是債務人流動性和償付能力未達到約定。維好觸發時,債券本身可能還沒有違約。反之,維好觸發點尚未達到時,債券也可能已經違約。
最後,所有的維好協議均會明文約定維好承諾幷非擔保。
所以,維好從法律上和實踐上與擔保均有明確的差异。讓律師出具維好不等同于擔保的法律意見應無困難。反之,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的律師,給出一個維好協議“有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實質構成擔保”的書面意見則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和豐富的想像力。
實務中,維好債券的投資人應不會堅持債券條款中包含辦理跨境擔保登記的約定。畢竟,維好結構的設計初衷就是避免外管登記。而《指引》關于“境內擔保人承擔法律性質甄別及登記責任”表述,是否會導致維好提供方被事後認定爲擔保方,因爲沒有辦理跨境擔保登記而遭到《外匯管理條例》、《跨境擔保外匯管理規定》以及《跨境擔保外匯管理操作指引》中關于違反登記規定的處罰呢?
如果企業事前取得相關的法律意見書,認定即將發行的維好債券不是跨境擔保,哪怕外管最終認定應該登記,對企業進行處罰或許也缺乏合理性。畢竟,如果外管總局要求所有的維好協議都進行跨境擔保,《指引》裏就不應有“具有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實質構成擔保”的前置修飾語。直接說明“維好協議須參照內保外貸管理”不就得了?
維好協議的條款經過十餘年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到了約定俗成的境地。只要項目律師不特意地去修改通用條款而進一步“加强”維好承諾,維好協議被視作跨境擔保而導致維好提供人被處罰的情况應該不會出現。
當然,處罰的裁量權在各地的外管。
三、維好結構在近期境外債券發行中的應用
2023年6月至今(2024年6月18日),共有67只中資境外債券采用了維好結構。其中31只爲金融租賃和證券公司 - 它們的信用堅挺,投資人可以接受維好增信的些許不確定性。
剩餘36只爲地方國企債券,其中17只同時亦有銀行備用信用證增信。對于這些債券而言,增信的主力是備用信用證,加上境內母公司維好支持的主要作用是向投資人標識還款來源,以便于投資人過會。
爲什麽不用母公司擔保呢?除了3只債券源自東營、日照之外,其餘14只債券均來自于外管登記困難的江蘇、浙江和青島。在有備證支持的跨境結構發行中,備證銀行通過RCPMIS等電子系統,向其所在地外管報送銀行提供的跨境擔保。如果發行人母公司也提供擔保,則一般認爲母公司還需在其所在地市的外管中心支局辦理跨境擔保登記。如母公司僅提供維好則不需要。
理論上,備證銀行進行電子申報不需要地方外管主動出具登記憑證,因此受到外管干涉的可能性較小。然而,這幷非絕對。例如建德市國有資産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原定于2024年5月9號交割的南京銀行備證+維好增信債券,就因爲備證銀行受到外管的主動指導,未能完成交割,最終交易流産。另外,《指引》第3.5.4.1(9)條規定:“同一內保外貸業務下存在多個境內擔保人的,可自行約定其中一個擔保機構到所在地外匯局辦理登記手續”。在“備證+擔保”結構中,備證銀行和母公司均爲境內擔保人,如果約定由銀行辦理登記手續,是否就完成了跨境擔保的登記責任?如果這樣,“備證+維好”結構還有沒有必要?直接用“備證+擔保”不行麽?
《指引》于2024年5月6日生效後,由南洋商業銀行(中國)提供備證的青島軍民融合發展集團有限公司點心債是唯一成功發行的“備證+維好”結構債券。維好提供人沒有辦理跨境擔保登記。在當前的監管條件下,特別是外管審批較爲嚴格的地區,只要投資人能接受,發行人或許還是更願意選擇“備證+維好”結構而避免“備證+擔保”伴生的外管登記不確定性。
自去年6月以來,地方國企發行的19只沒有其它增信措施的“裸發”維好外債更加引人注目。由于維好結構的信用弱點,一般來說,采用這個結構的是信用條件較好且位于外管較爲嚴格的地區的發行人–比如杭州。僅此一地就占據了19只“裸發“維好債券中的11只。杭州的信用堅挺,似乎也幷不需要爲采用維好結構而支付多少溢價。杭州上城區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AAA)2024年4月22日發行的2億美元1年期維好債券票息爲6.20%,較定價日美債基準的溢價僅爲1.07%。而2023年12月杭州市拱墅區國有投資集團有限公司(AA+)發行的7.1億元3年期維好點心債票息僅4.3%,也不比同時期AA+城投直發或者擔保發行的點心債更昂貴。我大杭州信用的强勁令人目弛神迷。
債圈人,不嘆生不爲杭州人,却應恨尚未發杭州債!
除了杭州、無錫這些强信用地區,一些其它發行人選擇維好結構就有些令人費解。青島海科控股有限公司的裸發維好在市場上漂浮了很久,2024年6月12日也成功發行了一單,但發行量僅5,400萬人民幣。這種高收益發行人哪裏來的信心選擇維好結構?聽說青島海科第二期維好發行正在醞釀中,而報給投資人的綜合收益率僅比類似的直發或者擔保結構債券高1.5%左右。這點溢價是否足够有待市場的檢驗。城投信仰是高收益境外債的邏輯和信心基礎,是以投資人都尋求一個“這是標債”的自我安慰。而裸發的維好城投債到底有多“標”,則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哲學問題。

四、展望未來
自2020以來的司法實踐已經充分詮釋了維好協議的法律效力:雖弱于擔保,但總體來說維好還是經受住了考驗。在跨境擔保登記存在高度不確定性的地區,維好結構有著天然的吸引力。《指引》是外管總局將部分維好納入監管範圍的一次嘗試,但目前似乎幷不意味著維好結構的終結。萬物或終有消亡的一天,但對于維好這個中資境外債發展過程中誕生的獨特存在而言,這一天還沒有到來。未來他將譜寫怎樣的新篇章,或許仍然值得期待。

